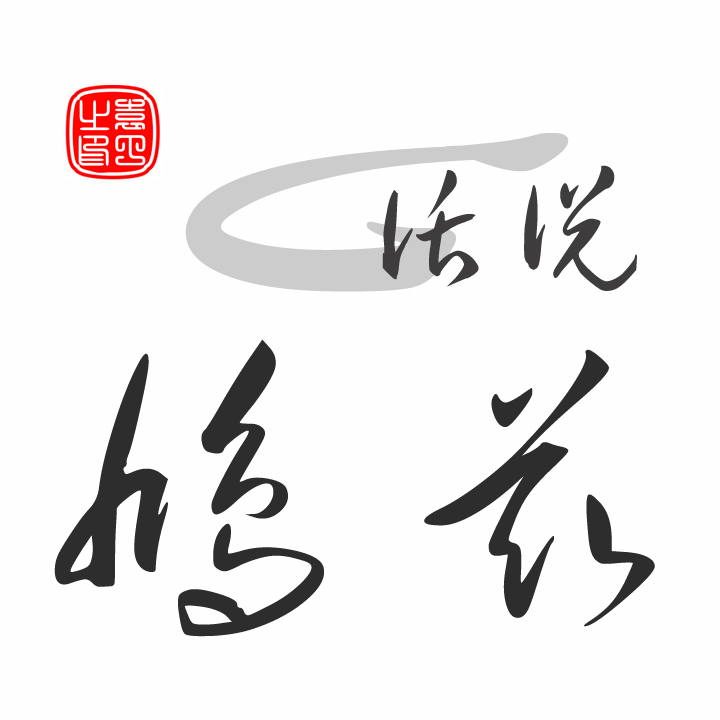北宋元丰七年(一〇八四年)阴历六月二十三日,年已四十七岁的苏东坡,带着幼子苏过,乘一叶扁舟自黄州(今湖北黄冈县)顺江而下,抵达芜湖大江口。在岸边迎候的人群中,有一个身穿袈裟,头戴毗卢帽的方丈,笑容可掬地走上前去合掌施礼。他,就是芜湖东承天院(后改为东能仁寺,遗址在今胜利电影院附近)的当家师,名叫蕴湘。苏东坡父子这次芜湖之行,正是应他的邀请,前来为刚竣工的玩鞭亭和梦日亭题诗的。蕴湘将东坡父子迎进轿内,一溜人马彩舆,便浩浩荡荡地向东承天院走来。
东承天院,金碧琉璃,轩阁栉比,香火旺盛,名响江城内外,与吉祥寺、普济寺、广济寺,号称芜湖四大名寺。这时,寺院内的楠木案上早已摆好砚、墨、笔、笺。东坡一进院,就走到案前,挥毫书下《湖阴曲》一首,其后还写下意味深长的题跋:“元丰五年,轼谪黄州。芜湖东承天院僧蕴湘因通直郎刘君谊,以书请书湖阴曲。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舟过芜湖,乃书以遗湘。”题跋交待了来芜的缘由,也隐约抒发了他当时的抑郁心情。原来苏东坡在元丰五年前一直是朝廷直史馆的翰林学士,因对北宋神宗期间的王安石变法持有反对意见,被贬谪到黄州担任一名不准签发文件公事的团练副使。于是他就懒于政事,筑一个称为“东坡”的读书室,号称东坡居士。从此,他的苏轼名字反而不如苏东坡响亮了。
苏东坡题诗完毕,蕴湘又向苏过合掌施礼道:“斜川居士是否也请赏光。”苏过字叔党,自号斜川居士,连连摇头说:“不敢放肆,不敢放肆。”苏东坡笑着说:“但题无妨。”苏过红着脸说:“儿岂敢在父亲面前班门弄斧。”满院中顿时响起一阵笑声。
苏东坡所题的《湖阴曲》是七言古诗,咏叹的事是“玩鞭春色”一文中所述的故事。它出自于《晋书・明帝纪》。在他题写前,唐朝的著名诗人温庭筠路过芜湖时已写过七言古诗《湖阴曲》一首,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芜湖之行时也题过七言古诗《湖阴曲》一首。苏氏兄弟和温庭筠的诗写得都很好,但由于他们承袭旧说,又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,句读不清,将应该称之为《于湖曲》的题目写成了《湖阴曲》。据《晋书・明帝纪》原版本书载,晋太宁二年(三二四年)“六月(王)敦举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骏马微至于湖阴察敦营垒”。许多人在读这段没有标点的文字时,由于不知芜湖过去因谐音关系又叫“于湖”的缘故,所以都错误地句读如下:“六月,敦举兵内向。帝密知之,乃乘巴滇骏马微至于湖阴,察敦营垒”。于是“于湖”变成了“湖阴”,并以讹传讹,因袭数世。实际上这段文字应句读如下:“六月,敦举兵内向。帝密知之,乃乘巴滇骏马微至于湖,阴察敦营垒。”后人经过考证,才作以上纠正。如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游览芜湖时,就特地作了一首七言古诗《于湖曲》,改正其老师的错误。清朝尚书黄钺的数十首词就定名为《于湖竹枝词》。虽然如此,人们还是习惯把这种七言古诗称为湖阴曲,并在这个基础上,形成江城梨园子弟的著名曲牌。
令人遗憾的是,苏东坡所写的《湖阴曲》一诗,如今已不复存在;蕴湘诗人刻的苏东坡这首诗的石碑,也因战乱丢失。只有题跋为时人相传,载在《芜湖县志》上。
苏东坡父子在逗留芜湖期间,还到芜湖河南韦许家中作客。苏东坡对韦许的“独乐”书室甚感兴趣,连声说:“我的书室叫东坡,你的书室叫独乐。东坡者,独乐也;独乐者,东坡也。”韦许见苏氏父子经济十分拮据,当即赠银百两,东坡拒不接受,韦许正色地说:“你右迁得势,我独乐居士仍独乐,不会巴结你的;如今你左谪受困,我独乐居士则不乐,何必礼让。”苏东坡为之动容,收下了他的馈金。东坡离芜后,曾和韦许保持通信联系,并题寄《傲轩》诗一首给他。这些珍贵的诗文尺牍稿,都被韦许的后代——清朝乾隆年间的翰林院侍读学士韦谦恒收进他所编辑的《旁搜集》一书中。此书如今已难见到,不知是否存世。